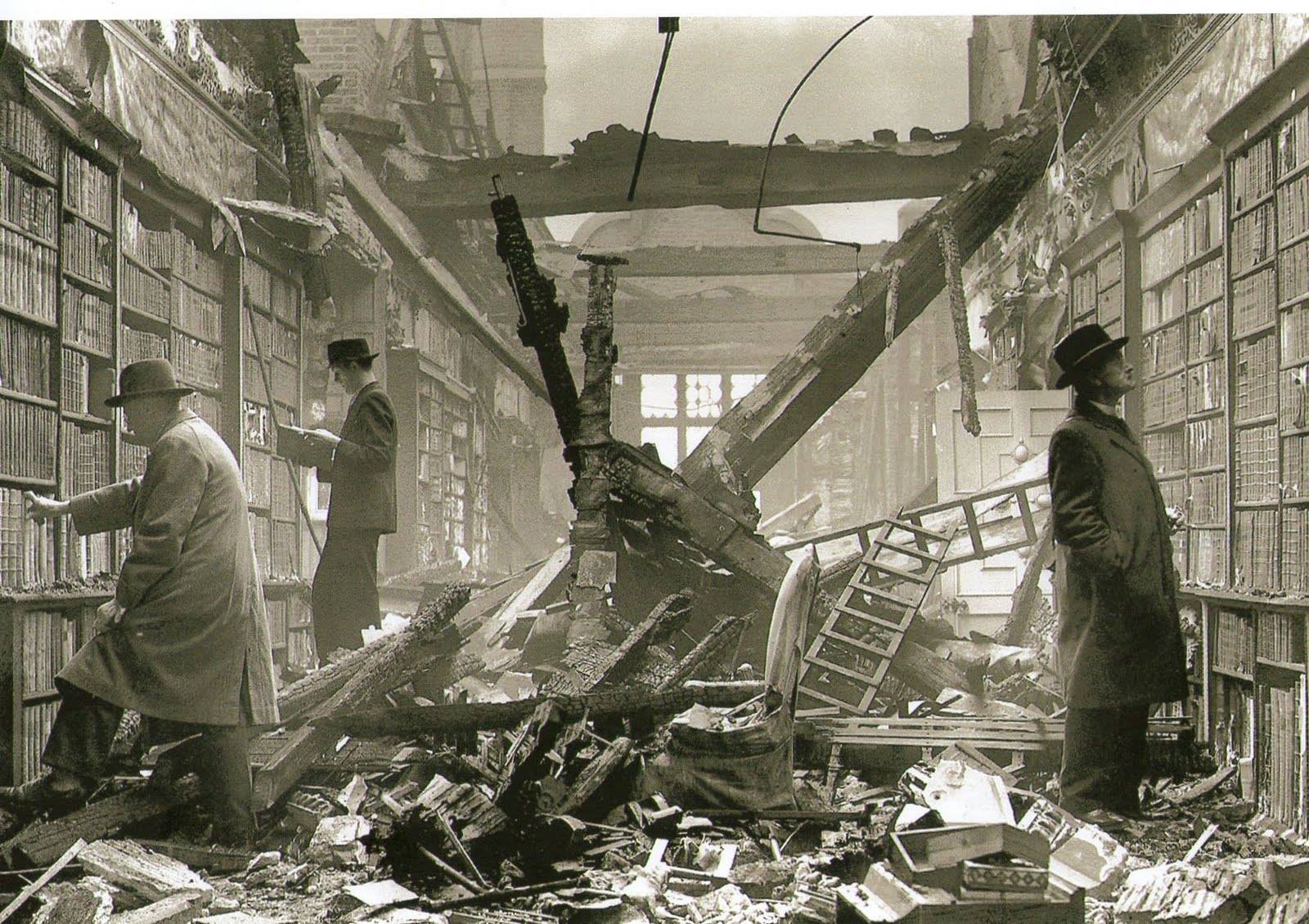2010年09月16日 00:00
《盛世:中國,2013年 》
陳冠中著
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272頁,HK$70
我曾經看過呂楠一輯關於中國天主教徒狀況的攝影作品:有聖方濟各修士在山間道上行走,有豫中地區牧民在荒野上牧羊,有農舍小房中做祈禱的老人,並深深為其中的宗教感所感動。 稍後有機會也看過他的另一輯關於中國精神病人狀況的攝影作品,這種感動有增無已。
後來在《讀書》上看過一篇楊念群有關中國歷史學從大歷史敘述轉型向區域社會史研究的文章,才明白這種感動的因由:活躍在我們身邊的歷史才是最真實的歷史,而社區就是真實歷史最可靠的載體。
在呂楠的攝影作品中,無論是天主教堂,精神病院,乃至稍後出現的中緬金三角罌粟種植區域,一個一個我們看到的社區場景都指向終極人文關懷,而不是天主教在華傳播,經濟改革釋出邊緣人口,中緬邊區遊擊戰爭的大歷史敘述。 呂楠用了一種幾近人類學家的眼光來反觀上層的運作,還原我們曾經熟悉但已經永遠失去的一種生活方式。
陳冠中小說中的社區場景也是一樣的多變:開篇是北京市區的三聯書店,三里屯;中篇是北京近郊的懷柔,五道口;終篇是河南焦作的教堂,探討的主題也是一樣的永恆:人際關係的疏離,信仰的失落到趨於神經質,理想主義的邊緣化。 與呂楠的影像比較,儘管經文字還原的物件有所重疊,但陳冠中最大的叩問可不是區域社會史,而是集體對六四消失的記憶。
他依然執著於大歷史敘述和大歷史事件的功能,在開篇劈頭一句便是「一個月不見了」,幾經上下求索,包括方草地和韋希紅久違後的出現,老陳在港台中的經歷,眾人齊集焦作溫縣教堂,以致綁架何東生以後從他口中說出的一段盛世危言,種種歷史敘述方式,都使人想起清末寫成的《老殘遊記》以史帶論的中國歷史學的傳統,且以「新盛世主義的十項國策獻言」終結歷史。 這種寓歷史於小說視野的做法,正是讓《盛世》這本書區別於國內同類型小說的根本原因。
中國對香港的「歷史想像」堪稱耐人尋味:一個外在非常現代化的世界都市,卻包容了幾近所有的中國時間元素。 筆者早期接待國內朋友的到訪,常驚訝於他們對香港傳統節假日的傾心,而不是林立的高樓大廈。 金庸根據故鄉海寧回憶的明清中國,黃霑填詞的中國背影,乃至周星馳「大話西遊」中草寇的中國,無一不是「翠袖寒香」的中國(張愛玲語),稍遇風雨,即土崩瓦解。 國內作家阿城初到香港,也驚訝於香港的元氣淋漓,直逼漢唐,而香港人則是明清人:民間社會的活躍,小共同體價值觀念的一致,語言文字追慕於古代。
相比於香港,中原文化卻因為過度「夷化」而失去溫柔敦厚的本質。 央視到今天還拍不出像黃日華翁美玲版「射雕」的金庸小說,流行歌詞也寫不出黃霑的「河山夢縈」,更不用說通過對粵語殘片的徹底顛覆後產生的一個荒原上的中國。 這跟物質景象的中國無關(國內版「神雕」用了浙江的雁蕩山做外景),也跟用了多少文學顧問無關,重要的是金庸的「歷史想像」一去不復返,剩下的徒有一個古裝的軀殼。
然而,更耐人尋味的是,當香港歷史併入中原母體後,香港文化一度激發的「歷史想像」卻很快被納入俗文化的範疇,金庸且被王朔昵稱為「四大俗人」之首,而一度構建起來的演義式的歷史敘述,包括「黃飛鴻」,「霍元甲」,「葉問」等技擊小說,逐漸消失在中國更為強大的「地理想像」當中,失去它此前特有的魅力。 到了「李小龍傳奇」中劇中人都用普通話對答,或「十月圍城」中通過孫中山之口解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道理,香港特有的「歷史想像」可以說是喪失殆盡。
取而代之的是國內「大國崛起」,「故宮」一類的紀錄片,因為其視像宏大,空間遼闊,反過頭來征服了香港相當多的觀眾。 而「雍正」,「康熙」等劇集,又因為影射台灣,當然引起天朝朝貢體系的更大的「地理想像」。
從周而復始的「歷史想像」轉軌到層圈式的「地理想像」,正正見證著中國為了適應民族國家的到來,從古老的「中庸」走向「均衡」的價值觀,而陳冠中小說汲取自國內多種管道的資訊,特別是201-261頁的「現實世界的最佳選項」,再演繹成小說後,讓「歷史的終結」(走向六四)變成是「終結的歷史」(走出六四),個中恐怕也有陳冠中不自覺的因素在起作用。
黃仁宇一度在國內走紅的《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或許為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一些線索。 中國近代歷史的轉型,無非是上層建築(國民黨)和下層建築(共產黨)構建的完成。 由此延伸,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其實和政黨政治有莫大關係,而政黨政治又與歷史學的生成有關。 其中最主要的是民國期間,利用西方進化論歷史觀修史,其效果是「歷史的終結」,因為假如歷史不奔向西方的「自由,民主」終點的話,則一切的抗爭都是徒勞的。
在這一方面,延安時代的史學家範文瀾可以說是總其大成,他的《中國通史》中緊扣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引領我們走向人類共同社會主義的未來。 這種情況到了新中國卻急劇轉型,從郭沫若發端的《蘭亭真跡》,《文姬歸漢》翻案文章,乃至後來的《李白和杜甫》,《甲申三百年祭》的另立爐灶,在「終結的歷史」的基礎上,郭沫若對傳統歷史的顛覆,正暗合當時「亞非拉運動」的橫的地理延伸,而不是縱的歷史繼承。
作為小說最重要的場景,陳冠中也著力於顯示北京的特質,但這並非明清五百年來的傳承,而是幾段故事形成的「地理想像」的軸線,以北京為中心,展現京港,京台,京美,京法,京豫等互為解讀的空間場景,因而使得故事的敘述從「歷史想像」轉身到「地理想像」最終成為可能。
關鍵的轉接點在於陳冠中接受政黨政治為正統(「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世界裡,一切都是最好的。」),因為只有政黨政治才能消解歷史差異做成的抵觸(嚴格來說,中國每個省區都有自己獨特的社會史和物質史)。 這與歷史發展階段無關,但與中國多元非一體的文化傳承有關,新儒家表述的「文化中國」最多是一個虛構的共同體,政治的整合才是中國民族國家形成的關鍵因素。
但吊詭的是,陳冠中小說中呈現的是一個向中心塌陷的「走向邊緣」的同心圓,而不是天朝朝貢體系的「走向中心」,於是,民族國家的邊界是遊走的邊界,民族國家的開啟和閉合也變成是「均衡」的地緣政治的結果。 與周邊國家比較,北京更像是一處窪地,其稠密度遠遜於軸線的另一端。 無怪陳丹青用「大兵營」來形容當代北京。 正是北京的荒涼,使得任何異質文化在這裡生存成為一種可能。
從「歷史的終結」的「歷史想像」到「終結的歷史」的「地理想像」,陳冠中的《盛世》為中國現代文學帶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提出的問題:在一個歷史業已逐漸消失的國度裡,文學還有沒有足夠的生存條件?
寫《荒人手記》的朱天文說過,當我們不再為明天的到來感到焦慮不安,文學就失去了它生存的意義。 中國當代的顯學是經濟學,因為這個學科的跨度最大,對人類的社會行為的預測也最為精準(儘管文學還有其內心尋索的意義)。
這使筆者想起年初到布拉格出差時,在一個書店窗櫥前看到高行健《靈山》捷克文譯本的瞬間感動。 扉頁是作者的介紹,封面則是作者非常著名的現代水墨畫,大點小點的墨暈鋪滿精裝本書面,下方有一仿佛行人的墨暈,遙望西南行旅的艱辛。 論者都以為是六朝志怪小說在當代的延續,時間座標竟不復存在,仿如沈從文的《邊城》,因其穿越時空而形成其不朽,直接使人想起福克納小說的美國南部田納西流域的故事。
從這層意義上說,陳冠中的《盛世》鉤起的應該不是明代短命的「隆慶新政」或清代長命的「乾嘉盛世」,它更確切指向的是一個「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世界」。
The Center for Place, Culture and Politics’ Annual Conference 2024:
Abolition and/as Activism
-
Friday May 3, 5PM-8:30 PM & Saturday May 4 10AM-8:30PM The People’s Forum
(320 West 37th Street, New York City) Register here for the in-person
conference....
13 hours 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