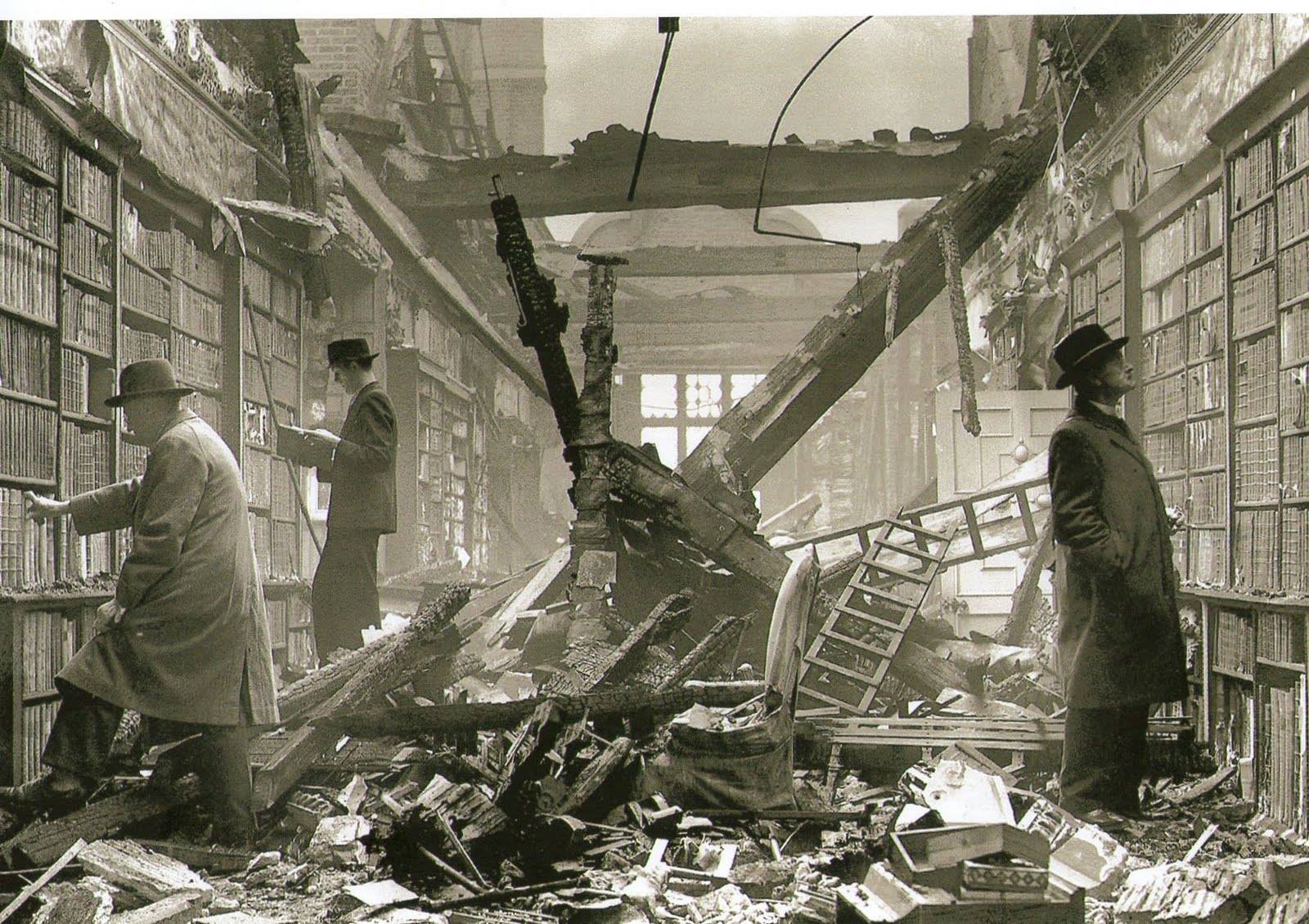打開書櫃

2007 年夏天,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出版了能夠讓人捧在手心細讀的小書《四代香港人》,不過在內容上,這本著作卻一點都不袖珍,藉它而引發的香港社會討論,在這兩 年多以來從沒休止,當中待發掘、待探討之處仍有不少。來到2010年,呂教授亦已移師陣地,從中文大學走進了香港大學,此刻與他坐於港大咖啡店再探四代香 港人之間的恩恩怨怨,新增與重拾的論述對本地不同世代的人來說依舊極具啟發性。
讀: 《讀書好》
呂: 呂大樂
讀: 《四代香港人》這本書,已經推出了兩年,你覺得它對社會有哪方面的影響? 它是不是變成了熱門的討論話題?
呂: 其實我自己並不是很用心跟進那個討論,部分原因是它與我原先期望出現的討論有所不同。我寫這本書原本是向第一代致敬,就是我們父母那一代。主要是因為當時我的父親過身了。
讀: 可是,出來的情況卻有點不同,討論變成了是對第一、第二代香港人的指責和控訴。
呂: 結果變成是第三、第四代站一邊,然後第二代人站在另一邊,當中不幸是第一代人沒有出現在討論之中。原本我想寫第一代人如何栽培第二代,以及第二代又可能重 新在第一代身上學到些甚麼,然後去幫助第三、第四代。但是這個現象卻沒有出現。部分原因是第二代人沒有參與討論,只有第三、第四代的參與,遺憾是沒有勾起 第二代人對自己和對父母那代的反思。
讀: 你認為第一、第二代人不參與討論的原因是甚麼?
呂: 我自己接觸到的第二代,大部分都不以為然,覺得沒有甚麼好討論。曾有位教授跟我說,你那本書好像很多人看的樣子,跟着他說,其實這很易理解,第三、第四代那樣糟,可是你就說成沒有問題,他們當然很喜歡!
讀: 你說第二代人對這個話題缺乏興趣,但第三、第四代人之所以熱烈討論,原因何在?是真的社會流動低了,還是只是一種感覺?
呂: 我經驗覺得是感覺多於social mobility(社會流動性)低了。我自己對社會流動、社會分層的研究,例如2006年那個數據便指出,社會依然是有流動的機會。
讀: 若然在客觀上工作機會沒有減少,流動的渠道仍然是開放,那為甚麼第四代人會借這本書宣洩了他們不滿?那種感覺從何而來?
呂: 我相信有兩個原因,第一,你可以想像一個十多二十歲的年青人,在長大的過程中會聽到很多雜聲。你身邊不斷會有人告訴你,你一定要這樣做,要那樣做,不然就死定了。現在有很多這些聲音,以前相對較少。
讀: 可能是由幼稚園開始的吧。
呂: 由幼稚園、小學,跟着到大學。入到大學,有人會告訴你要怎樣作出選擇,要特意去「上莊」,要去找些地方做點東西,然後去找internship,借意去找 個mentor。總之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都要去儲齊它們。現在很多這樣的聲音,是很擾人的,你會感覺到那種frustration。

讀: 這種frustration,也許比起沒有晉升流動的機會更嚴重。
呂: 因為晉升流動機會的煩惱一直存在嘛,你我都試過廿多歲,都應該知道。我也會同情部分第四代或第三代末的人,對於我那代,去到30歲可能就真的起飛,而且起飛的幅度還很大;但是現在部分人會覺得到了30歲仍是差不多,沒有明顯分別。
讀: 我在《明報》看到梁振英寫了幾篇文章,談social mobility和青少年工作等等,他提到一個觀點,他覺得八十年代高流動性和起飛是例外,即是Perfect Storm Theory,幾樣條件巧合同時出現。最主要是84年前途問題,跟着就是人才外流和移民潮,同時經濟擴張,那麼就變成你剛才所說,到了30歲之後就 「boom」一聲準備彈起。其實,根本就不是一代壓迫一代的問題,而是客觀上香港發展的一個階段,一些特殊的條件造就了八十年代的booming?
呂: 但那個booming的出現,又不是只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其實已開始。你可以說現在很難會有同樣的高速增長,但我覺得七、八十年代讓人舒服的原因,不純 粹在於一個量的問題,多元路徑也很重要。現在的年青一代當中,出現了兩極化的情形。如果我發現一個「叻」的新一代,我必須承認他比我讀大學的時候「叻」。 他們的認識比我們多,他們的英語口音好和exposure都比我們多。
讀: 說到frustraion,第四代香港人當中最frustrated的一群,是大學和副學士畢業的那一群。
呂: 我看到的就是有一部分人,若你將他們放在七十年代的環境下,他們並不能上大學,中學畢業後可能已經出來工作了,可能在做merchandiser,又或者做teller之類,只不過現在他們變成了學位人士而已,因此與路徑收窄有點關係。
讀: 我的印象是,在七十年代後期,香港有很多偷渡來港的新移民,他們會「盡地一鋪」,在街邊賣水餃也好,或者在酒樓做兩年,之後便自己開餐廳。
呂: 以前和現在有點不同,以前香港人很相信:「我不理你學歷,只要你打得就可以了。」譬如說在以前的娛樂圈和文化界,小學畢業也沒有所謂,以前我出來寫稿的時候,有很多編輯也不是大學畢業的。我最初出來寫作的時候,在報社裏大學生是少數來的。
讀: 其實這是任何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這種屬粗放式成長,好像現在的中國大陸一樣,只要打得就可以,不理你是工人還是耕田出身。直到發展至某個成熟階段,就會開始講學歷講資格,然後大家就會要在拿到那個資格之後,才可以由那個平台起步,那就是到了另一個階段。
呂: 可以說是,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我們自己本身被不必要的制度化。在經濟上由粗放型變成秩序型,是會收窄了某些空間。經濟開始成熟,增長速度會開始下降,這 當然是有制度方面的因素。但是,當中亦有部分人為因素,譬如面對轉型,有需要將所有人才市場都納入一個學歷系統裏面嗎?其實,一個頂尖的世界城市,在文 化、藝術、時裝設計方面等等,它都不是遵行單一套大學制度;它需要可能是某種學歷,但不是純學歷。
讀: 可能是設計資歷,不是綜合大學學位。
呂: 對,那不是學位來的,大家要知道那個行業,需要哪種東西。但是現在的香港,無論是文化或經濟發展,我們將很多的東西都收集在一起,將全部都變成了一個學歷制度,而且還是同一款大學式的文化和學習方式,像現在我們連工業學院也沒有了。
讀: 會不會是參與競爭那些人本身的問題?從小到大已經被灌輸一種策略性的行為,去選擇升學和就業,去選擇甚麼科目等。將來若果發現自己不能達到預期目標,怨憤就出現。過去那個年代的人不同,他們不跟主流遊戲規則玩,只依自己的遊戲規則玩就好。
呂: 問題與兩代人都有關係。第一方面就是後生的是否有膽量抽身出來,用自己的方法去闖,去衝擊它。但同時你會面對一個處境,坦白的說,第二代還活於現在,依然繼續在無須受到挑戰和威脅情況下,繼續延伸他們的遊戲規則。
讀: 因為他們是主流吧!
呂: 是主流。我有一個比喻,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問題。我們並沒出現新生產力,不像當年美國。美國最初在克林頓上台前,Generation X是有很多憤怨的,在政治上、經濟上沒有出路。你看Reality Bites那套戲,大學生出來最初就只是賣時裝和做店員,其實都一樣如此。
然後有Internet Boom,跟着其他很多方面都出現了大轉型,於是便出現了新生產力,會有些東西是只有這群新人懂得,以前的人不懂。但是香港現在的煩惱是,我們不斷在重複去做一個商埠。
讀: 問題是Youtube也好、Facebook也好、Twitter也好,最開始的Amazon也好,其實它都不是大型的資本運作。背後都只是一群人,在自 己的車房中自己製造出來。但是internet革命中的那些business model,着重的不是的科技,而是idea,如何執行idea。所以到了第二代末的香港人,我會覺得是他們的問題,是沒有那種執行創意的能力,沒有了決 心,只希望跟着那個主流遊戲規則去玩,但是又想快點贏,一切變成IPO玩意。第一、第二代的執行能力是很強,又或者是如他們所講的純粹是role play。
呂: 第二代的執行能力是很強。
讀: 如果你要超越他們的話,就要擁有和他們一樣的執行能力,但要比他們更加creative。
呂: Creative之餘更要夠膽去做一件東西出來,不只是在說其他人有甚麼不足。從我的角度來說,如果第二代還在要求自己進步的話,我覺得他們要搭道橋出 來。不然的話,我面對的問題就是連我生活中的事也開始重複,就連自己都覺得悶。如果你想看到事情改變,就會有一種力,這是由第二代散發出來的。到了那時, 你又會不會搭道橋讓別人來撞一下自己,讓新的力量出來?
讀: 這不會發生,很簡單以CR為例,如果我是俞琤,無論如何都會找回葛文輝和林海峰。第一是那由我自己創造傳奇;第二就是我有權;第三他聽我話,不會「起我飛腳」。
呂: 所以到了現在我們還是在聽同一樣的東西。
讀: 十多年前我們聽軟硬《老人院》,到現在廿年後,依然還在聽。但當你想一想,在商台如果再選下一級,就會是I Love U Boyz,這時你會發現俞琤的選擇未必是錯。他們連「搞gag」也不好笑,執行力比不上林海峰,於是我們連少許的收聽動機也沒有。
呂: 我相信要在第三、第四代裏找,總可以找到執行力比較強的人。
讀: 在流行音樂方面,當Beyond出道的時候,沒有大公司支持,他們第一張唱片就失敗,第二張唱片就變成亞拉伯跳舞女郎,弄得古靈精怪,連原本的fans也 對他們不滿,主流樂迷又不接受他們。他們經歷過兩、三年的掙扎,四個人差不多連食都沒有得食,後來才有一、兩首主流的情歌,開始紅了起來。他們都不是因為 大公司,也不是因為參加甚麼音樂比賽,如嘉士伯流行音樂節等被發掘。
呂: 他們出現的時間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同一時間出現達明、出現樂隊熱潮。
讀: 問題就是,我從來不相信黃貫中的結他技巧是無法被取代的,沒有人可以勝過他。但是為甚麼到今天你還是沒找到一隊樂隊的結他手可以勝過他?這個問題就等於問為何同樣有人「搞gag」,卻未能勝過林海峰?責任在林海峰?在俞琤?還是在I Love U Boyz?
呂: 我依然相信這是兩件事,坦白說句,你肯選多幾個,肯試多幾隊,自然就會有多點機會。但是若果最後結果都是沒有的,那就不關別人的事了。我的重點是,第二代自己都覺得很悶。
讀: 第三、第四代人以為,他們無需要經歷一個去鍛鍊他們執行能力的年代,以為只要讀完演藝或理工的multimedia出來,就可以立刻埋位,他們不會理會許鞍華也好,徐克也好,就算黃貫中也好,都有過一段相當長的日子當nobody苦捱。
呂: 答案可能是,在23至35之間的一個調整。現在很多第三、第四代看到的,是第二代於30歲之後的遭遇,但是卻看不到他們在23至30歲之間的遭遇,那就是人人在埋首苦練的時候。
讀: 他們的執行能力就是從那裏來的吧。
呂: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確是比較有利的。有一次我和冼杞然談起,我在讀大學一年班的時候已經在中學教書了,亦有在大專界或青年中心演講。那個年代又真的很奇怪,沒有甚麼人會理你在幹甚麼。
讀: 討論發展下去,會不會變成一個推卸責任的問題?當然你說第二代沒有反省過,但是第四代和第三代香港人有沒有反省過?是他們太早放棄?他們要在主流之內成功,就必然要面對第一、第二代的主流坐在那裏──即是說陶君行必然要面對華叔。
呂: 從社會學上來說,我們六十年代的時候其實也一樣很多frustration。
讀: 我想五、六十年代的frustration很簡單,任何年青人對主流社會和建制都會有不滿。有獨立思考的人,學校年代就已經會培養出一種反叛的行為、反叛的思想。有一段時間可能你會出來參加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
呂: 有時候當你講frustration,那件事未必一定要發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是看到有這件事情存在。
我覺得社會是有惰性的,這個惰性部分來自第二代,他們鼓勵不到新的事情出來。至於第一代,他們走過難,打過仗,對某些東西的看法很不同,他們寧願自己沒有也要給下一代。
讀: 即使第一代本身有很多成就也好,總會覺得下一代人讀書比他多?
呂: 對。這就是第一代的特點。
讀: 他們會尊重讀書的人。
呂: 但是第二代不是,第二代的人覺得自己讀書比人多,所以就將下一代框起來。這就是我覺得為何會開始出現惰性的原因。
讀: 但其實可以集結勢力去將這些東西改變。例如五區公投,你既然覺得民主黨代表了第一和第二代香港人那種建制精英的看法,他們永遠都在建制當中玩;你是可以另立旗幟的。
呂: 對,但很不幸地,其實五區總辭也只不過是一些激進的第二代的一個遊戲。他們始終都走不出那個框框。他們都是建制派來的,就算總辭,最後都一定要返回建制當 中。此外,第三、第四代都走不出這個框框。作為社會學家的,當然會嘗試去想在甚麼環境之下,他們會走不出這個框框。
讀: 相對其他國家,香港在這方面有着一種特殊性,還是都一樣?
呂: 在制度上說,我覺得其他地方和國家始終某些條件很不同。
讀: 是政治問題還是其他問題?
呂: 有時候會有一種機制催促你去迫人上台,英國政壇很明顯的吧。因為之前那群人已弄到一團糟,大家說來說去出不了新東西來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新的議程,無論你 說甚麼都好,我們就有了這樣一個決定。你剛才說Youtube也好,internet也好,都是走這樣一條路線,就是應用新的idea。
讀: 你覺得最重要的分別在哪裏?是我們的政治制度停滯,令我們沒有人才更替,帶領不到社會變革?
呂: 我覺得沒有輪替是一個問題。香港社會的輪替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輪替。當董建華在推行某些政策的時候,他找了一些經濟專家做智囊。之後換了人,卻都是那一幫。自由市場的時候是那幫,不是自由市場的時候也是那幫。這和美國不同,你是民主黨,我是共和黨。
呂: 可能由1976開始到大概83年中英談判附近,那時候是最天馬行空,百花齊放的,無論做甚麼也可以,你做甚麼社會都有反應。但是到《英雄本色》出現之後, 就出了問題。好像《英雄本色》就是文化的天堂。資本運作到了84年之後又是另一個天堂、炒樓又是一個天堂、政治又是一個天堂,所有的東西出現了一個整整齊 齊的香港模式之後,就再無需移動似的。
讀: 就是因為太成功。
呂: 回想之前,其實那也是有點不可思議,實在是厲害。一個爛鬼地方操作的事情,還有人去模仿學習。
讀: 是不是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普及文化及中產階級文化的發展?
呂: 不止這樣,你想想大部分地區的開放改革模式都是一樣,興建的第一座大廈一直要是圓形的,一定要有旋轉餐廳。22層和27層的旋轉餐廳,就是用回香港合和的 模式,而且還相當之多,差不多去到任何地方也是這樣。每個城市要證明自己現代化就是要有旋轉餐廳。我們當時改變了很多東西,因為實在太成功了。
讀: 這也跟希望將一切凍結在八十年代的心態有關。
呂: 是有關的。
讀: 那即是說,我們不需要世代交替?如果當時已是最成功模式的話。
呂: 但在97之後,發現那不是最成功。
讀: 是社會變了吧,香港人從來不講美學問題。第二代人是不關心這些事的,大會堂和康樂大廈等,他們會覺得沒有問題,蠻好看。問題是現在那一代人關注的重點不 同,他們看的世界多了,他們知道北京有一個鳥巢,有個建築師叫Herzog,或者知道巴黎有一座建築物是可以這樣子興建的。
呂: 部分是這樣,部分是在97之後的不景氣,破壞了原有最成功的模式,沒有人再相信。
讀: 所以新的情況就沒有出現。
呂: 所以我才要寫《我的2047》,因為若果再凍結,在哪兒都不行……
讀: 但是問題其實是新的難產,社會對此沒有共識,也沒有甚麼衝擊。
呂: 衝擊很多時是來自第四代香港人。
讀: 像反高鐵運動,嶺南文化研究學系或義工,已經不是菜園村的人,像何芝君、司徒薇他們。但在入面投票的那群人,不論政黨其實都是第一、第二代心態,是發展功 能、效率導向的香港人。若沒有辦法令到這些人進入主流的討論中,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不是說吸納他們進去,但起碼大家都要有討論的機會。
呂: 還有就是在主流位置的反對力量,是否可以建制之下,夠膽和建制派開火?但是現在我是看不到很多。要進入當中,用可以和他們對話的方式去對抗。
讀: 現在他們用上了道德精神勝利法。
呂: 現在大多數人都選擇這方法。我們以前是受「老毛」影響,我們要走到群眾去說群眾說話。會說你們這群人貪慕虛榮,飽食終日,所以我不理你。以前會覺得必須要走入群眾,讓群眾聽得到你的說話,你才算成功。
讀: 但會不會欠一個世代交棒的潮流式?經過大選如奧巴馬,然後好像是一支旗號,有一個號召作用,然後影響到其他層面。
呂: 問題是,香港直到今天,走出來選舉的那班人,全是第二代。難聽一點說,你在自己的組織裏也做不到一個這樣的趨勢。
讀: 或者你要跟隨着做第二代的,即是甘乃威模式。他要等到上一代不做了,他才有機會上去。
讀: 第四代需要有一個自己的身分吧。
呂: 要有一個獨立的身分。
讀: 否則你永遠也是甘乃威、或余若薇與陳淑莊。就算是陳淑莊也不會想過,要當今次民主運動中的主角,或是借這個機會去擺脫余若薇的陰影,憑自己團結、甚至成為一個新的世代,一個新的民主運動,她未必有這個想法。
呂: 問題是,我看不見有一個獨立的身分。
讀: 看不到。所謂的「新民主運動」,也只是一個sound bite。
呂: 現在的討論層次是想像不到的低。
讀: 現在根本就不清楚,又不能說他們完全反對走議會路線。
呂: 因為所有人也留了一手。
讀: 對,就是第二代人sure win,risk free。
呂: 但其實應該是這樣的一個鬥爭。
讀:你應該說如果我選不到,我就2012年也不選。
呂: 應該這輩子從此就不參加,以後都就在外面,不回來。
讀: 也許,第二代香港人的問題就是甚麼也要sure win。
呂: 但這是一個慣性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強的傳統。

讀: 香港的東西就是永遠有潛規則。不單只政治、民主、選舉,其他事情也是。表面上是搞文化產業,實際上是IPO。表面上是代際交替,實際上是「收」。表面上是包容,實際上是想吸納他們,想去改變他們的看法,而不是接受他們的看法。
呂: 我想個別人士是以為自己正在接受的,不過沒有一個獨立的議程。
讀: 本身以為自己很另類的人也是正在找尋主流社會影響及認同。
呂: 這才是令我覺得很不安的地方。我有時會說,你跟他決裂就決裂吧。
讀: 可是他們又要sure win。
呂: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很完整的決裂可以自圓其說,倒是沒所謂,只是另一種生活方式。其實我挺喜歡1978年以前的左派。
讀: 就是完全不參與主流社會。
呂: 自己看自己的電影,自己參加自己的旅行團。好像自己給自己說一次話一樣,也挺好的啊。可是現在不是這個樣子,反而更尷尬。你一方面說你不玩,不過只限今次。
讀: 就是我跟你決裂,不過只是一會兒吧。
也 許,香港人很怕失去自己的身分。就算入到議會也好,他覺得精神勝利法也是很重要的。你看得到,他實際上是在參與建制,可是他仍然是用一種建制外的 mentality在建制裏玩。現在的問題是,無論你政治上怎樣努力去推動改變也沒有用。例如政府發展優秀產業,你看得到,不論是年青一代的香港人也好, 還是企業家也好,他們心中只是想如何把廠廈包裝成酒店。除此之外,我真的不覺得他們有甚麼可以engage社會然後一起去做。這認為這個情況會改變嗎?
呂: 我想要換一批新的人才可以了。若要博一博的話,我也不介意讓年輕的一輩試一試。就算做不了甚麼,也願意博一博。我看不到現有的反對系統班底可以出到甚麼有趣的東西。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困了在這裏。
讀: 我想你是少數,有反省能力,才會覺得悶。第二代香港人不會覺得悶。
呂: 第二代香港人不會像我一樣覺得悶,可是他們用另一種方法表達出來。例如我最近去了深圳一趟,跟同一世代的人,都是一些很成功的人。你會發現很奇怪的,就是他們看了深圳所有東西也說好,我覺得這是一種釋放焦慮的方法。
他們就是覺得香港不行。於是另一方面,他們就說深圳甚麼也好,有很多地方我也忍不住問:這樣也好?事實上,大陸很多建築物也是大而無當。高不等如好啊。這種甚麼也是好的心態也是很可怕的。
讀: 如果用他們的核心價值來看的話,他們一定是覺得內地比我們好。高鐵從廣州去武漢走380公里只需三個半小時,以前大概20小時吧,他們當然覺得很神奇。只有容易收地的國家,才能建一條這麼直的鐵路,但第二代人不會想這一點。
呂: 所以你是很實質的見到,第二代表達焦慮的方法就是大陸甚麼也說好,然後就是說快,「你看人家多快!」他們不會想別的問題,這是他們的表達。他們就只是覺得 我們慢,但問題是他們又忘了我們慢的原因是甚麼,為甚麼我們要慢,為甚麼我們要去處理。他們當然不會覺得悶,可是他們的焦慮就是我們甚麼也比人慢。人家的 東西又快又大又漂亮,好像很厲害,可是一年後倒塌了,又當成另一回事。
讀: 內地差不多每月都有最大的按摩休閒中心開幕,為甚麼呢?因為他們的東西一個月之後就很殘破了。然後就有一個新的按摩中心來取代舊的。
呂: 有一次我在上海,在那最新、最高的Hyatt喝東西,向下望,我真想不到,怎麼浦東這麼快就破落成這個樣子?
讀: 你看東方明珠塔附近,那裏才開發了沒多久,怎可能這樣殘破?你看看深圳地王大廈那裏,建築物很快就很破落了。你再看深圳的地鐵,才建了三年。你覺得如果主動吸納更多年輕人的話,可以改變這個狀況嗎?除了令他們沒有那麼frustrated之外。
呂: 我覺得應該多給他們機會。如果我是領導公民黨的,面對一個這樣的政制,就無謂戀棧了,就給一些比陳淑莊還年輕的人上去試試,看看有甚麼改變。
讀: 會不會是他們很快就建立了一個思維模式,就是效率至上,覺得用這麼少時間選一定選不到,會失去市民的支持,知名度不夠。於是如果想用最少的時間選贏,結果還是派了舊的人出來選。然後又墜入了功能效率的思維中。
呂: 一定是這樣的。但如果他們願意走這一步,我認為會有新的生命力。
讀: 舉例說,請了一班副局長、局長助理。其實對那班政務官來說,他們更是不願放手給他們。
呂: 我覺得更奇怪,是到了第三、第四代也參與批評陳智遠的時候,他們仍然在運用第二代人的角度。
讀: 說到最後,不是社會上某個人設計了一個制度,令社會停滯不前。你看陳智遠的問題就最清楚了。批評得很狠的人就是來自同代那群人。
呂: 這當然是很不幸的。
讀: 這不是不幸,而只是冰山一角。
呂: 所以我一直說第三、第四代根本沒有一個身分,沒有一套獨立想法。
讀: 根本這是一個集體意識問題。如果這是一場Generation War,你應該把陳智遠捧為你們的教主。
呂: 對,如果我仍是廿多歲。我一定捧他為教主。
讀: 為何不行?由二萬人工一跳而變成十多萬人工,有何不可?
呂: 根本就覺得很應該。還覺得應該多開幾個位給我們。你用另一個角度想,他以前一表人才,在現有的大學制度來說是如何糟蹋了他,哈哈。
讀: 其實這個惰性本身是體現在香港人的性格之中。
呂: 這種性格不是第三、第四代獨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代也有。
現在整個社會也是risk free問題,政改出現問題的時候,「掟蕉」是最容易做的事。大聲一點說,起碼到現在我們仍然有幾個人在寫一些文章去說政治委任制度是必要的,只是應談論 怎麼去「優化」,次次也給人狠批的了。扒逆水永遠是辛苦幾十倍的,「掟蕉」就容易成為話題了。
讀: 可是對社會發展沒有幫助。
呂: 這也是香港其他方面的問題,香港很少想共同富貴繁榮的想法。我常舉的一個例子,Harry Potter這書推出時,英國文化界、媒界的反應是大家一起捧它為教主。之後大家心底裏一起說:唓,其實這本書沒有多厲害。這是很多其他國家的做法,如果 一旦成功了,就大家有份有着數。我出來捏死你,其實只是捏死了另一隻螞蟻,大家也沒有得益啊,當然是捧你出來對大家有利。其實奧巴馬也是一樣,社會上覺得 如果出現一件新事物,社會上就要說新的事情,要有新的議程。大家自然有新的機會,有些人可以翻身,起碼可以一試。可是香港不是一個這樣的地方,就是要把你 擊敗了才算。
讀: 可是香港的精英也不會有這樣一種意識,就算是不同年紀的精英,他們也沒有一種齊齊成功的意識。
呂: 現在就好像去冒險樂園一樣,有空就玩玩射擊遊戲,無限復活。不過人會死啊。我不相信第二代可以永永遠遠下去。但當第二代死了,如果再由第三、第四代去延續,然後我們發現他們說的話、做的事原來也是一樣的,事情就真的會很糟了。
讀: 但這很悲觀嘛,需要等年紀大那一班人死掉……
呂: 那死之前也會慢慢老的。沒辦法的了,唯有看年輕的一代有否這種挑戰的能力。
讀: 那你是否應該寫一個續篇呢?
呂: 名叫《第二代香港人》嗎?就只集中談論第二代!哈哈。其實是值得的,因為《四代香港人》爭議並沒得到第二代人的參與,因為內容不中聽嘛。
讀: 對呀,對於你預期出現但最後在討論裏面沒出現過的東西,包括第二代裏面成功的香港人,他們怎樣看這個問題。